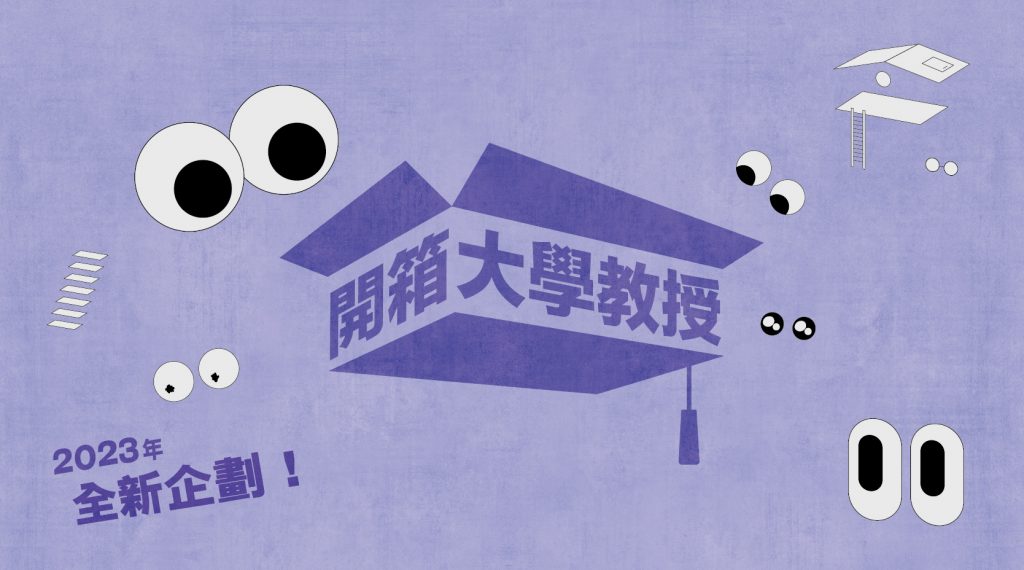醉心於野生動物的保育學家|臺大昆蟲系曾惠芸副教授(上)
動物是我的最愛
採訪、撰文|韓喬融
審訂|曾惠芸 教授
曾惠芸老師目前在臺大昆蟲系擔任副教授。她從小就熱愛各種動物,並且相當確定她喜歡與野生動物相關的工作。不過,當時的她並不認為一定要走學術研究這條路。於是,她曾多方探索並嘗試她所感興趣的工作,先後在臺北市立動物園、農業部生物多樣性中心(前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),以及位於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任職。正因如此,惠芸老師累積了豐富野外調查、野生動物研究以及博物館研究經驗,具有如此豐富野外調查和博物館經驗的教授在臺大並不多,而這些寶貴的經驗恰巧得以應用在她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。在昆蟲系任教的她,除了研究可愛的球背象鼻蟲之外,近期她開始拓展研究領域,想要進一步了解都市化對於周遭昆蟲或是動物的影響,再從這些領域拉回自身,嘗試找到野生動物和人類和平共存的合適解方。
從小熱愛動物並確立志向
一切都要從惠芸老師的孩提時光說起。從小,她就鍾情於各種動物。當時家裡有很多關於動物的百科全書、圖鑑及相關的人物傳記。惠芸老師十分喜歡閱讀這些圖鑑,甚至會做筆記。此時,她對動物的興趣在心中逐漸扎根並萌芽。雖然家裡除了養魚以外並未飼養其他動物,但這並未削減她對動物強烈的好奇心。小時候,惠芸老師會把零用錢存起來,一得空便就跑去水族館或是鳥店買爬蟲類、烏龜、鳥、寵物鼠等動物來飼養。其中一個深刻的回憶是,她曾經存錢存了許久,終於買到一隻六角恐龍(一種蠑螈)回家養,她細心照顧,定期為牠購買魚類餵食,但不幸的是,有天餵食時,牠意外噎死了,令她感到相當遺憾。然而,正是這些照顧動物的經驗,使她從小就確定了自己的熱情所在與未來志向。
在回顧這些過往時,惠芸老師提到,家人當時的態度相當關鍵。她坦言,她的家人雖然沒有太多接觸動物的經驗,有時甚至會感到害怕,但卻未曾阻止過她飼養動物,甚至願意讓蛇或蜥蜴在家裡活動,並勉強接受她將路殺動物包好後拿回家冰存。雖然他們心裡擔心這興趣在未來可能沒辦法謀生,但家人還是願意支持她的所有決定。
好奇心引領她探索未知——和昆蟲、夜鷹與野保所的偶遇,以及分子生物學的挑戰
從小到高中,惠芸老師對動物的熱愛始終如一。然而,當時她自認對昆蟲所知甚少。她自覺既然對昆蟲了解不多,不妨嘗試深入學習這個尚未開發的領域,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於是,大學時期,惠芸老師選擇就讀中興大學昆蟲學系。在學習昆蟲學的過程中,她發現昆蟲確實是一個極好的研究材料,並因此開啟了她的野外調查之旅。即便如此,她依然對脊椎動物情有獨鍾。所以,大學畢業後,她決定進入中興生命科學系,研究她從大學時期便感興趣的一種鳥類——臺灣夜鷹。
雖然臺灣夜鷹並不屬於保育類鳥種,但在當時已被列入瀕危鳥種圖鑑中。不過,關於這種鳥類的相關資訊和研究仍相當稀少。此外,當時臺灣南部的臺灣夜鷹族群較為穩定,所以必須到屏東進行研究,也結識一群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(野保所)的朋友。幸運地,因為這段過往,她在屏東野保所結識的朋友至今仍是她重要的研究夥伴。在研究夜鷹期間,曾發生過一些有趣的事情。例如,有一次颱風天她準備前往溪床觀察臺灣夜鷹,由於牠們是夜行性動物,所以必須傍晚就下切到溪床待命觀察。那次似乎有人和警察通報疑似有人想自殺,為了安全起見,一群警察一同下來搜查,場面極為壯觀。儘管這是一場烏龍,但成為了珍貴而有趣的回憶。
然而,那段研究時期並不順利。由於需要在臺中和屏東之間來回奔波,調查工作也多由惠芸老師一人獨自進行,雖然她喜愛這份工作,但身心俱疲,難以承受。因此,惠芸老師在進行了一年的臺灣夜鷹研究後,主動向指導老師提出希望更換實驗室的請求,指導老師也理解並同意了。不過,在當時的中興生科所內,從事野外調查的實驗室不多。惠芸老師最終換到分子生物學實驗室,唯一的野外採集工作是去魚市場撿下雜魚。這樣的轉變對於她來說充滿了痛苦和挑戰。她曾經對分子生物學相關知識心生抗拒,但這次卻不得不面對。為了適應新的領域,她修習了大量的分子生物學相關課程。她提到,當初面對一篇幾乎每個字都查過卻仍然看不懂的論文時,壓力非常大。她常常忍不住偷跑去賞鳥或與朋友和學長姐進行野外調查,故經常受到碩士班老師的斥責。由於學習的內容並非她所喜愛的領域,她花了四年才完成碩士學業。
走哪條路都沒關係──但我只想做我喜歡做的事
儘管碩士班過得相當辛苦,卻也因為這樣的經歷,讓她可以順利地找到她的第一份工作。
她慶幸當時自己有努力撐過去,同時感激當時指導老師扎實地研究訓練。畢業時,她正巧從學姐那裡得知臺北市立動物園的爬蟲研究有空缺,剛好需要一位能夠進行野外調查及DNA實驗的人,從而順利應徵上了這份工作。在動物園的日子,她感到十分愉快,並積累了豐富的爬蟲類研究經驗。後來因緣際會下,她聽說南投農業部生物多樣性中心(前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)的爬蟲室正在徵助理,需要有兩棲爬蟲類與分子生物學的技能需求,因此她也順利地接下了這份工作。在生物多樣性中心工作了三年後,惠芸老師感到自己所做的計畫和研究內容逐漸趨於單一,因為個性使然,她渴望挑戰新的研究議題或方法,恰逢科博館有技術人員的職缺,也順利的轉換工作環境。
對於未來,惠芸老師較少有長遠的規劃,但她一直以來都目標明確──這個目標並非希望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,而是希望自己持續前進和進步,更希望能夠在自己喜歡所熱愛的事情上一直樂在其中。無論未來走哪條路,從事何種職位,走上學術的道路也可以,但她的原則很簡單──她只想做她所喜愛的工作,僅此而已。

九年的博物館歲月──計畫之外的博士班旅程
回到臺中後,惠芸老師再次開始進行實驗和野外調查。當時東海大學有一門她感興趣的課程,於是前往旁聽。儘管身為旁聽生,她仍認真完成所有作業,這樣積極的態度引起了林仲平老師的注意,老師因此詢問她是否有意攻讀博士學位,而她也希望能有目標讓自己進步,所以開始攻讀學位。幸運的是,科博館的工作性質和內容和她的博士研究相關,主要工作內容都包括野外調查、採集和製作標本、標本館管理、協助策展、規劃展覽內容、導覽人員訓練,以及協助研究員進行各項研究。當時的黃文山主任全力支持她的研究,只要惠芸老師有把交辦的工作如期完成即可,其餘時間都可以自由運用,並鼓勵她在學業上繼續精進。正因如此,惠芸老師得以在科博館擔任技術人員的同時,攻讀博士學位。她自認花了長時間工作,每天待到晚上近午夜,然後隔天早上再打卡上班,日復一日,卻樂此不疲。
對惠芸老師來說,當初決定攻讀博士學位的初衷並非為了追求學術生涯,而是單純希望能夠自我提升。她希望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來激勵自己,持續努力,朝著這個目標前進。
與球背象鼻蟲的相遇──爬蟲類和昆蟲的結合
惠芸老師博士班的題目以球背象鼻蟲為主角。該題目的選擇源自林仲平老師正在研究的菲律賓角蟬。角蟬和球背象鼻蟲有點像,牠們很容易停著就不會動,也不趨光。林仲平老師經常看到球背象鼻蟲,所以認為這樣的題目應該可以做。儘管當時幾乎沒有人做過球背象鼻蟲,但惠芸老師也同意這個研究題目應該具備一定的可行性,進而選擇了這個較為冷門但有趣的議題。
雖然題目有趣,但在採集或實驗上的難度極高。牠們不易繁殖,從卵到成蟲的存活率僅約1%,且生活史長達半年,透過與動物園的合作,成為了世界上最早突破這些繁殖困難的團隊之一。現在再回頭來看,惠芸老師認為林仲平老師具有遠見,儘管曾經沉寂了一段時間,但近幾年關於球背象鼻蟲的研究在許多國家正逐漸興起。
回憶當時經歷的困難,惠芸老師笑著坦言,野外調查的艱辛與在實驗室會遭遇的截然不同。雖然兩者都十分辛苦,但出野外的時候很不一樣的是,還要忍受身體上的苦──吃不好、睡不好及蟲咬等。在這樣的狀況下,若仍然能夠感受到對工作的熱愛,那些辛苦便值得付出,這份熱情讓她得以繼續堅持下去。
此外,惠芸老師提到,科博館的環境對她幫助甚大,尤其是來自同事的支持和鼓勵。在野外採集時尤為重要。球背象鼻蟲的採集困難重重,尤其在面對經費和進度壓力時,同事們的鼓勵和安慰極為關鍵。她感覺自己的情況比較特殊,由於工作性質與研究相似,且得到上司的認同和支持。在科博館工作和研究過程的一切進展都相當順利。